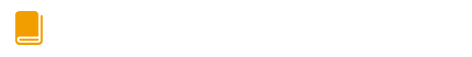
 剧本app下载
剧本app下载
 剧本公众号
剧本公众号

上个月,在汤子馆与朋友小聚时,有人说起了郑跟脚。说他在城边那个四合院的门外,重新砌起了一面墙。
多了一面墙其实算不得新闻,什么时候砌起来的,也不是新闻。但朋友一再强调,这面墙是郑跟脚自己用一块砖一抹水泥精心打造而成。郑跟脚在这面墙上画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各种色彩纠缠,交叉,浓淡无序。究竟画的是山是水还是人,没有一个人能分辨,有说二维的,有说三维的。后来有人指着墙,说墙里藏着一个女人。一时间,好奇的人纷纷来到这面墙,左看右看,看不出一丁点名堂,有些小主播或者小网红还把这面墙当作打卡地,不过,这些人翻来覆去只把自己看得一头雾水,最后的评价就一句,娃娃撒尿,胡乱淋得。我在高中时也曾学过画,感觉对一幅画多少也会有点认知和见地。
有一次路过,我也站在这面墙前仔细观察了个把钟头,结果把我看得云山雾罩的,从构图,色彩到表现手法,我看不出任何值得欣赏的妙处,只能悻悻回转。有一次,文化馆一个美术学院出身的资深工作人员路过这面墙,竟然在此逗留了小半天,低头仰头,左右摇头,而后频频挠头。引得路人齐齐整整地站在这面墙前,也学着那位资深工作人员,长嘘短叹。业内业外的人,懂画的和门外汉,都频频穿梭在这面墙前,用些时尚的词汇品评此画,更有甚者,还拍照发抖音,把郑跟脚与西方一些绘画大师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朋友一再强调,说郑跟脚常常一个人对着这面墙念念有词,常常声嘶力竭,有时会对着墙持续砸上几拳,而后去医院包扎双手。郑跟脚独自堆砌的一面墙,然后再把自己绕进墙里,多少有些怪异。每次向郑跟脚探讨这面墙的奥秘,郑跟脚总是笑而不答,生出一副文化范儿。这面墙到底呈现的是随性涂鸦还是暗藏着玄学之类的东西,没人说的清。
郑跟脚以前是我的工友。当年我们都在县城一家鞋帮厂上班,当时的体制叫大集体,郑跟脚能写能画能识图,干活舍得力气。郑跟脚有个特点,做事没有边界感,想起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不计后果,无论自己几斤几两,懂还是不懂,只要拿起家什,上手就干,至于干好干坏,他都从不在乎。郑跟脚因为偷盗边角料被厂长开除了。后来,郑跟脚便在街头找了一块空地摆摊卖鞋。他原本有名字,自从卖鞋后,人们就开始叫他郑跟脚。我们当地人买鞋试穿,不说合适或者舒服,从老辈传下来的一句,叫跟脚。老郑卖鞋,人们就顺口叫他跟脚。郑跟脚与正跟脚谐音,里面暗含着与鞋相关的一份吉利。
郑跟脚光棍一根,伶仃大半生。他除了吃饭,就是专心琢磨怎么靠卖鞋发财。他卖过真鞋,假鞋,奇鞋,怪鞋甚至私人订制。他被工商局罚过款,被买主撕过脸。时间长了,人们还是觉得郑跟脚卖的鞋不但样子奇特,而且舒舒服服的,的确跟脚。郑跟脚竟然发迹了。他在我们凤城好几个楼盘都买了楼。他的店面也不断扩大升级,还雇了一个一只眼有玻璃花的女孩当服务员。他店里有玉石茶台,一把不许任何人触碰的紫砂壶,茶台上摆放各地名茶。他每天来店里摇着薄扇,咂几口茶,然后就反剪双手,在步行街悠闲踱步。
踱步时就有些文章了。他会突然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向一个方向看。他会在原地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刮风下雪都不会让他移动身体,眼睛也从不离开一个方向。街上的人都知道他富贵,腰杆像桥墩,个别人背后说他是吃饱了撑的,大部分人还是矮矬矬排在他身后,助攻一样跟在他身后一起望着一个方向。
有钱了,郑跟脚又在城东草河区城乡结合部花重金购买了一块地,建起了四合院。关于郑跟脚重金购买的这块地,的确有些来头。其实,郑跟脚重金购买的这块地,就是我们当年一起工作的鞋帮厂的原厂址。至于郑跟脚为什么挖空心思买下这个废弃的老厂房,我猜想这与他的一段情事有关。
鞋帮厂地处低洼地带,厂外靠近一条公路,公路的路基高于厂房地基,这样,厂房一到汛期就常常受水气。厂长就在靠公路一侧砌起一面墙,一则用来挡水,更重要的是在这面墙上套红了鞋帮厂的几部联系电话和代表企业文化的宣传标语,因而具备了广告功能。开始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关注这面墙,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墙根来了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漂亮女人,这面墙转瞬之间成了鞋帮厂一道热门景观。
这个女人什么来路,多大年龄,谁都不清楚,有人说她是一个走街串巷挑担卖茶叶的南方妹。这个女人就依托这面墙,支起了一个杂货铺摊位。
我们那个时候荷尔蒙分泌过剩,又因为这个女人不是坐地户,我们一帮愣头青每天都盼望早点下班,去女人摊床前买瓶汽水就着一个茶叶蛋,边吃边与女人搭讪。往往是这样,我们每个月那点工资几乎有一半都去了这个女人的口袋。开始的时候,搭讪的小伙子多,苍蝇一样围着摊床转圈圈,可没过多久,仅剩下了一个人,就是郑跟脚。
我们得来消息,知道这女人是厂长养着的女人,住在厂长包住的宾馆。厂长外出谈生意,这个女人就收摊跟老板在天上飞。我们知难而退,都清楚去厂长的**那儿刮油水,迟早要进油锅。郑跟脚却一条道走到黑。下了班就来到摊床前,吃着茶叶蛋喝着汽水与女人对坐。我曾劝郑跟脚离开这个女人,可郑跟脚铁了心要靠住这个女人,并扬言非得从这个女人身体里掏出一个豪华婚礼还要掏出一窝孩子。
摊床的地潮湿,郑跟脚便从厂子的垃圾桶里挑选出废弃的边角料,用缝纫机扎制成简易地毯,并且在简易地毯上画出 36 码的各种脚印。郑跟脚心巧手巧,又捡来碎步条,扎制成 36 码拖鞋,逼着女人在摊床的椅子上摇着脚晒太阳。
女人说自己在南方常常打着赤脚,郑跟脚就从凤城各个商店为女人买来各种款式的鞋子。要女人穿上,在椅子上摇着脚。但凡女人蹙眉头或者轻轻喟叹,郑跟脚就会蹲下身子为女人揉脚,直到女人说出了“乖娃”两个字才肯罢手。郑跟脚跟工友讲,女人的身材像过水面,生出孩子,肯定个顶个是演员的胚子。有一天,这面墙上贴了二十几幅照相馆洗印的大照片,都是郑跟脚在厂子里捡拾边角料,扎制地毯扎制鞋垫和鞋子的现场定格。结局只有一个,郑跟脚被鞋帮厂来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接下来,郑跟脚依然风轻云淡,像一贴膏药,天天粘在这个女人的摊床上。女人劝他趁着年轻有体力,找个姑娘暖日子。郑跟脚就在下班后去火车站货场轮扳锹装卸车皮再挣一份工资。每次挣来钱都为女人买最时尚的鞋子。女人穿着新鞋坐在椅子上摇着脚的那一刻,郑跟脚就当着女人发誓,他说他或者在某一天把厂长用麻袋套了沉入西大河,或者在某一天自己成了有钱人就盘下鞋帮厂。
有一天,女人手里攥着两张火车票,问郑跟脚敢不敢跟她去南方浪迹天涯。郑跟脚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女人。女人说自己已经打定主意带着郑跟脚私奔。两个人就来到火车站,准备乘倒数第二趟火车离开凤城。
郑跟脚做事决绝,早忘了父母和人世牵挂,揣着户口簿就跟女人来到候车室。女人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突然对郑跟脚说,她忘了一样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东西——郑跟脚为自己买的那些鞋子。
女人说快有二百双了,自己把这些鞋子打了一个包装,必须一起带到南方去陪她浪迹天涯。女人说这个包装就落在摊床那儿,死也不能落下。女人急得两眼泛红,就差没涌出泪水。郑跟脚说这些鞋子代表自己的一颗心,落下了,情感也就缺少了重量。郑跟脚答应自己立刻返回到摊床去取包装。郑跟脚出了候车室,女人跟出来,一个劲儿朝着郑跟脚晃着手中的两张火车票。接着对郑跟脚反复叮嘱说,不用着急,一双鞋都不可以落下,一旦误了车次,她会找站长改签,她会在候车室一直等郑跟脚扛着包装赶过来共同乘坐最后一趟列车。
郑跟脚之前是一个几乎没有出过远门的人,等他扛着包装再次走进候车室的时候,值班员让郑跟脚离开候车室。郑跟脚说他是乘最晚一趟火车去南方的乘客。车站值班员说,之前开出站台的那趟火车就是最后一趟。郑跟脚找遍了车站的男女厕所,找遍了车站所有角落,也没有找到那个女人,他望着黑洞洞的远方,听到了火车嗷嗷叫。后来我跟郑跟脚喝酒的时候,郑跟脚会一直说自己的睡眠不好,一到夜里,耳朵里就会跑出一列火车,嗷嗷叫。
失去了女人的郑跟脚怒拆了墙根的摊床。每天晚上当最后一趟列车出站的那一刻,郑跟脚就会用拳头击打那面墙,直到双手血肉模糊,整个人再像疯子一样高举着流血的双手冲向医院急诊室。那时,我在鞋帮厂负责分发布料。我为了赚外快,每次都空报一匹布。这事最终被人举报,厂长就把我下放到车间去干挣钱最少的脏活,还在职工大会上扬言,说我是留厂查看,随时都会把我扫地出门。我就时不时在深更半夜用喷灯涂改那面墙的电话号码,还经常把鞋帮厂涂改成破鞋厂。我学过素描,画过人物,有几次,我用喷灯在墙上喷出了厂长和女人,还涂上一些污秽词语,直到有一天被派出所带走。进了派出所,我一直不承认墙上的画是我喷的。几个警员把我反扣在暖气片上,让我晚上仰躺在派出所的水泥地上。快到半夜,我冻的浑身发抖,于是,我决定彻底妥协。就在这时,郑跟脚来到派出所,他大包大揽,承认那面墙所有的事都是他干的。结果,郑跟脚为我挡了枪,去了拘留所,随后被鞋帮厂开除。
后来,鞋帮厂倒闭。
据说厂长登上一列火车,再无音讯。
再后来,郑跟脚靠卖鞋发迹,挣下若干桶金,实现诺言,盘下了鞋帮厂这块地。
原来的那面墙,已经斑驳陆离。有人在墙上贴小广告,写一些粉笔字,有人用黑色素涂上刻私章做假证的电话号码,孩子们则在墙上面粘花瓣,画怪兽。
郑跟脚固执地用高价买下这块地,交款当天的第一时间,他就雇来破碎球,砸倒了原来的那面墙。
很快,郑跟脚又凭借一己之力在原地重新建起了一面墙。
他自己先后买来了十几桶各种颜色的涂料,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对着这面墙反复粉刷,并且开始在墙上作画。画完了,一个人独自面对这面墙,反复斟酌色彩,忽而摇头,忽而点头,做完这一切,他又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上面不停地摇脚。摇脚摇累了,又取来清水把画冲洗掉。再画,再用水冲洗掉,反反复复。到底要画什么,要冲洗掉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终于有一天,大功告成。一面墙色彩混杂,眼睛,鞋子,森林,火车,繁星,河流,胡乱堆磊在一起。人们看到郑跟脚在一个黄昏对着这面墙持续站立了几个小时,那个深夜,附近的邻居都听到了郑跟脚的哭声。
之后,有人说,他们偶尔会看到郑跟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走出四合院,稻草人一样面对着这面墙,每次都会对着这面墙站上几个小时,那种恓惶,那种孤独,让旁观者瞬间想起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哀伤的章节。
附近的邻居说他是因为钱多,烧残了大脑。有的邻居猜测,说他可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我的其他朋友攒个酒局,他也经常找借口推掉。有时候,我们当中也有人会去那面墙前逗留一会儿,朋友们讲,站在这面墙前,如果用一定的时间观摩墙上的画,心里就有了异样的滋味。我们都在往老的年纪里挪动鞋子和脚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也越来越边缘化。彼此互致问候时,都是挣扎在前列腺肿大群落里的落魄住民。喝顿酒,剔剔牙,蹲在商场台阶上看着穿梭的往成熟方向奔波的女孩,只是心口颤一颤,更多时候是无动于衷。有段时间,我也被低质的日常折磨得焦虑不安,有一次路过这面墙,我也停留了许久。可我没有从这面墙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我的情绪在这面墙上一直不起波澜,更不曾自由宣泄。有时候我把自己装扮成郑跟脚,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面墙,除了眼花缭乱,除了被风吹出眼泪,更多是呆滞和木然。我几乎荒芜了我的当下。早些年还想兑现青春时的理想,到如今,我却把自己的生活拆解得七零八落。要钱钱不多,要名名没有,像一粒尘埃混迹在这个城市里。朋友越来越少,圈子越来越小。撒尿湿裤衩,枕着工资卡。白天晒太阳,黄昏喝趴下。我不知道我来这个城市究竟为了什么,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终会失去什么。高楼林立,白云流转,街衢喧闹,树木繁华。而我,孤独地游走在这里,我有时觉得哪些日益抬升的建筑像一波波滔天的巨浪,把我打翻,冲洗,送到深不可测的时间深处,等待未知的遇见和别离。
春暖花开,我朋友从叆河抓到了开河鱼,其中有两条三斤左右的花鲫子,难得的河中上品。约郑跟脚,他却一口回绝。平日里,郑跟脚最喜欢吃东北的开河鱼,见到花鲫子,两眼瞬间泛红。这种鱼无论多大,多贵,他也一定搞到手,求城里最有名的厨师给酱焖。他有句口头禅:人活一张荒唐皮,舍命不舍开河鱼。
至于为什么郑跟脚拒绝了这次酒局,我们都猜测不出缘由,人过中年,贫富差距,社会名分,理念差异,都会异化朋友的情感。郑跟脚举手投足间,多少也会呈现几分贵气,这又多少让我们这些昔日好友心存芥蒂。人世间,一些细微的变故,都可能让情感稀释或者蒸发。
我们吃着河鲜,喝着我们当地窖藏四十年最有名的凤城老窖,自找话题,抬升酒局的气氛。乘着酒兴,大家开始说起乡野趣闻,坊间臆断,陈年旧事,俄乌冲突。从东到西胡侃一通后,有人把话题引到了郑跟脚门店那个一只眼睛有玻璃花的服务员身上。总算迎来一个爆燃点,大家东爪西鳞,七嘴八舌,最终拼凑了一个共识,大家认定郑跟脚与这位服务员近水楼台,必有一腿。
只有一个朋友摇头。
他问我们,在这条街上,有谁听到过从郑跟脚身上传出来的一字半言的风骚趣闻。
在酒局上抛出一个噱头,而且无头无尾,最能勾起别人的好奇心。
我们非要这位朋友说出其中原委,我们愿意自罚一杯,在且听下回分解之前营造出仪式感。
这位朋友说,郑跟脚前几天在另外一个酒局上喝高了,我这位朋友主动把郑跟脚往家送。可郑跟脚靠近这面墙的时候,再也没有挪动脚步,而是斜躺在墙根,像尊卧佛。当晚起了大风,郑跟脚被风吹过,禁不住酒力,一直干呕。他搬来一块石头,让这位朋友坐在石头旁边,他说石头不走,朋友就不能走。郑跟脚回家又拿来酒杯和一瓶酒,他求朋友与自己对饮,不醉不休。郑跟脚忽而唱歌,忽而哭泣,最后非要跟朋友倒一倒心头的苦水。
最初,郑跟脚摆地摊的宗旨就是为天下的女人准备最跟脚的鞋子。买卖初期,生意惨淡。郑跟脚就搭起一个简易棚子用来固定地摊的位置,向周边摊位宣誓领地主权。可左右摊主一直都在排挤郑跟脚,白天搭起的棚子,晚上就被推倒。
遭遇挑战的郑跟脚找来三角铁,拉来电焊机。偷偷选择一个没有月亮的半夜,决定焊接一个结实的新棚子。那时一个女孩看中了郑跟脚,前脚连后脚地粘着郑跟脚。那天半夜,这个女孩偷偷来到郑跟脚摊位上,执意要给郑跟脚搭把手。女孩来之前,郑跟脚已经用水泥将三角铁浇筑在地上。本来应该在地上把棚子的框架焊接好再立起来,可郑跟脚怕四根立柱又被左右摊主给破坏掉。只能用水泥早早将立柱固定住。郑跟脚拿来椅子准备站在椅子上焊接几根横梁时,才感觉一个人确实干不了这活儿,实在是缺个帮手。
郑跟脚卖鞋有门道,可干其他活完全就是门外汉。郑跟脚又搬来一把椅子,他和女孩都站在椅子上,女孩戴上手套用手把着三角铁,郑跟脚顺手操起了焊枪。
郑跟脚从没有使用过焊枪,根本没有焊接经验,更不懂焊接会带来什么风险。当郑跟脚将焊枪死死抵住三角铁的一刹那,弧光四射,焊花飞溅。女孩惨叫一声,捂着眼睛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从那天起,女孩像是人间蒸发。
郑跟脚疯子一样找遍所有地方,连蚂蚁藏身的地方也要掘地三尺,可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这个酒局因为一段往事瞬间消弭了原有的气氛。我们几个人的眼睛好像在这一刻被焊花灼伤,各自呆呆地望着不同方向,彼此的心口似乎都生出了痛。酒局散尽,我有些茫然,不知道是该回家还是在这个城市漫无目的地兜兜转转。之前,我曾无数次在这个城市漫无目的地行走,直至碰到一堵墙或者其他什么障碍物,才坐下来仰望天际。每次我都孤独地想跟自己说话,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听听自己这副皮囊里面的声音。我骑着踏板摩托车,全身燥热,一阵又一阵的凉风拍打着我的脸和耳朵。我突然偶发奇想,我决定去郑跟脚的那幢四合院,我想突击检查一下,看看郑跟脚拒绝酒局到底是被什么牵绊。顺便看看这位富人舍弃酒局到底找到了什么胜于酒局的替代节目,是不是狡兔三窟,在四合院金屋藏娇,顺便也印证一下说他有严重抑郁症的传言。
踏板摩托车走起来声音很小,我慢慢接近了那面墙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远天零星闪动着几颗星星。附近有个铸造厂冒着烟,遮蔽了视野。在我靠近那面墙时,我影影绰绰看到那面墙前站着一个人。凭感觉,那个人就是郑跟脚。大晚上不睡觉,一个人面对一面墙,是思过还是渡劫?我悄默声把踏板摩托车停在一个木堆旁,蹲下来,我兴奋得想笑出声。我得仔细观察一下,看看这个达官贵族究竟在耍弄什么把戏。
我到这面墙附近的时间,郑跟脚只是对着这面墙发呆,直直地站立。我正估算他会站多久的时候,郑跟脚忽然对着这面墙砸出了一拳。
接着我听郑跟脚在小声喊叫,语速飞快,具体喊叫什么,我却怎么也听不清楚。
我观察一下四周,烟雾缭绕,我的眼前变得模糊,但我隐约听到这面墙周围,传来哭声,似乎有许多人在跑动。
这时,郑跟脚再次对这面墙又打出一拳。这一拳似乎重了,我好像听到了骨折的声音。郑跟脚继续喊叫,声音由大变小,越来越含糊不清。连续的喊叫声里渐渐多出了几分嘶哑。随着喊叫声突然停止,郑跟脚的双拳一起砸向墙体。闷响过后,我看到这面墙的中间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接着从缝隙中冲出一个人,这个人直接奔我冲来,抓住我,撕开我的身体后,像水蛭一样钻进了我的身体。
我全身剧痛,汗毛倒竖,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变成钢丝。我跨上踏板摩托,疯狂冲向远处。接下来,踏板摩托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再后来,我的身体变得飘忽,子弹一样炸开。朋友们纷纷带着水果来医院看我。确切地说,我撞上了一堵墙。
最后一个来医院探视我的是郑跟脚。他来病房的那一刻,我眼睛肿成了一条缝,身体的疼痛瞬间提升了几个等级。郑跟脚用手背贴着我的脑门对我说,人都该往亮处走,你干嘛非要一门心思撞南墙呢。他往我的枕头底下塞进一个大红包,并且约定等我出院后,一定请我喝窖藏四十年的凤城老窖,吃河中上品花鲫子。
他走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赶忙问其他朋友,我要确定一下郑跟脚的两只手是不是都缠着纱布,打着石膏。朋友说,郑跟脚照例那副牛逼样,反剪双手,一把折扇,慢条斯理的的贵人步。朋友说,从病房到进入电梯,郑跟脚一直哼唱着歌曲。
至于我问的双手缠绷带打石膏一事,朋友哈哈大笑,说我肯定是被一面墙,撞残了大脑。
那一刻,我的头好像被什么重物击穿,像突然破裂的西瓜。
专业定制代写小品、相声、话剧、舞台剧、戏曲、音乐剧、情景剧、快板、三句半、哑剧、双簧、诗朗诵、演讲稿、微电影、动画等各类剧本。联系电话:13979226936 QQ:652117037 公众号:原创剧本网-剧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