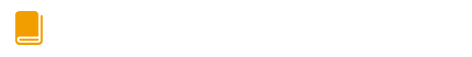
 剧本app下载
剧本app下载
 剧本公众号
剧本公众号

那条泥巴路被雨水冲出深深浅浅的沟,两旁土墙根长满了狗尾巴草。每年过年回村,我的脚都会不自觉地拐进这条巷子,停在那扇熟悉的木窗前。巷口老王家的收音机正飘着歌:“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调子悠悠的,像浸了二十年的月光。窗棂褪了色,糊窗的报纸换成了化肥袋里衬,可我总能看见她十二岁时的模样——坐在门槛上喝粥,嘴角沾着饭粒,抬头看我时眼睛亮闪闪的:“等等我呀!”
我们同岁,从光屁股玩到小学毕业,整整六年形影不离。她家门前有棵梨树,春天开满白花,风一吹就像下雪。每天上学我都要从她家窗前过,她总在吃早饭。有时塞给我一个温热的煮红薯,或是几把炒瓜子。我们一路小跑着去学校,书包在身后啪嗒响。她跑得比我快,两根黄毛辫子在晨光里跳,辫梢红蝴蝶结像团小火苗。
小学毕业那天,我们在村口打谷场交换礼物。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她给我一颗玻璃弹珠,里面嵌着红黄蓝三色花瓣。“对着太阳看,可好看了。”她神秘地说。我送她一本新笔记本,扉页用铅笔工整写着:“祝前程似锦”。那时我们都不懂,有些人的前程,就像没来得及开的花苞,风一吹就落了。
暑假过后,她没去镇上的中学。我每天故意绕远路从她家门前过,木窗总是关着。窗台上的凤仙花开得正艳,却再不见她探出头来笑。母亲说她爹在采石场摔伤了腰,家里欠债,她得去省城的纺织厂做工。我开始在她家窗外等,放学后的黄昏,周末的清晨,梨树叶沙沙响,像她没说出口的话。偶尔见她娘提着药包匆匆进出,看见我,只是轻轻摇头,眼角的纹路里全是苦涩。
十八岁那年过完年,我跟着村里人去广东打工。临走前,我鼓起勇气敲了那扇门。开门的是她娘,背驼得像张弓。“阿姨,小芳在哪?”她娘眼睛一红,摇摇头:“那孩子命苦,你别问了。”门轻轻合上,吱呀声像根针,扎得我心口发疼。
在东莞电子厂,我站在流水线前,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直到手指发麻。宿舍挤着十二个人,夏天像蒸笼。睡不着时,我就摸出那颗玻璃弹珠,对着窗外工地的灯光,看里面模糊的花瓣。二十岁那年,我托老乡打听到她在省城纺织厂的地址,写了封信。信很短,就问她还记不记得那颗弹珠,过得好不好。投进邮筒时,手心的汗把信封都洇湿了。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信石沉大海。我想,她大概早忘了我这个儿时玩伴,忘了巷口的梨树和弹珠里的花。
时间推着人往前走。我结了婚,妻子是隔壁生产线的工友,贵州人,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们有了个女儿,取名“芳芳”。妻子问为什么叫这个,我说,春天生的,听着暖和。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想起那个跑起来辫子一跳一跳的姑娘,想起她说“对着太阳看,可好看了”,那份感情,深埋在心里,像箱底那颗弹珠,蒙着时光的灰。
三十二岁那年春节,我带妻女回老家过年。年初三,我又鬼使神差地走向那条巷子。梨树还在,粗壮了不少,枝桠都伸到窗台上了。她家的木窗开着,一位白发老人坐在窗前晒太阳——是她娘。“阿姨......”我轻声唤。老人慢慢转头,眯眼看我很久:“小军?”
她颤巍巍站起来,从屋里拿出个锈铁盒:“小芳留给你的。”铁盒打开时吱呀作响,里面是我送她的笔记本,扉页上“前程似锦”已经泛黄。本子里贴着糖纸、邮票,夹着干花瓣。最后一页,整齐叠着那张我小时候给她包伤口的手绢——洗得发白,但干净。手绢里包着那颗玻璃弹珠,还有封信,字歪歪扭扭,像左手写的。
“小军,我知道你每天在我家窗外等。我右手被机器轧坏了,再不能写字。这信我练了很久。你的信我收到了,可我配不上你了。我订了婚,是厂里的保安,他不嫌弃我的手。别等我了。那颗弹珠,你要对着太阳看,可好看了。”信纸右下角,有个深褐色印记,像干涸的血。
这时老王家的收音机又响了,还是那首《窗外》:“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老人哽咽着:“那孩子,为多挣点钱给她爹治病,每天加班到深夜。机器把右手卷进去,三根手指没了。她不肯见你,是觉得自己残缺,配不上你。嫁人后跟丈夫去了外省,八年没回了。这本子她一直带着,前年才托人送回,说要是你回来,一定交给你。”
我握着弹珠,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里面的三色花瓣在光影中旋转,把二十年的时光都浓缩在这一瞬。远处传来妻子的呼唤,她在灶间帮母亲备年夜饭,女儿的笑声像银铃。我们都走上了各自的路,像两条相交后的直线,越走越远。
去年秋天,我收到从外省寄来的包裹,是本相册。第一页是她和家人的合影——她站在中间,微微笑着,右手自然地藏在身后。她胖了些,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还是亮闪闪的。照片背后写着:“我们都好,希望你也好。”
今夜月光很好,我坐在阳台翻那本相册,楼下不知谁家又在放《窗外》。我摩挲着掌心的弹珠,忽然懂了,有些爱就该留在记忆里,像弹珠里的花瓣,永远鲜活。就像她十二岁的声音,总在风里轻唤:“等等我呀!”
专业定制代写小品、相声、话剧、舞台剧、戏曲、音乐剧、情景剧、快板、三句半、哑剧、双簧、诗朗诵、演讲稿、微电影、动画等各类剧本。联系电话:13979226936 QQ:652117037 公众号:原创剧本网-剧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