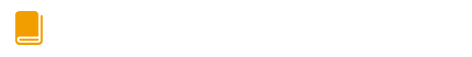
 剧本app下载
剧本app下载
 剧本公众号
剧本公众号

湘江的水汽总带着铁腥气,温温的,像老工人掌心磨出的茧子味。李砚踩着老冶金厂的碎钢渣往三号档案室走,鞋底卡进一道钢缝时,他恍惚看见三十年前的父亲正蹲在这里,用手指一点点抠出缝里的锈渣:“钢这东西,哪怕碎了,也得清干净,不然会硌着后来人。”
手里的黄铜钥匙硌得掌心发疼。钥匙柄上冶字的刻痕里,嵌着点暗红的钢花,师傅周正明临终前,用拇指反复蹭着这道刻痕,氧气管在嘴角晃荡:“小砚,这钢渣是1993年你爸焊高炉时溅的。当时他护着我,自己胳膊烫了个大泡,还笑着说老周,这疤能当兄弟印。”
师傅递钥匙时,指节上那道深褐色的烫伤疤正渗着血。他另一只手死死攥着李砚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个弥留之人:“去三号档案室最里头的铁柜,里面有你爸的涡轮壳图纸,还有我们当年没做完的模型……别让这东西跟咱厂的老机床一样,被湘江的雨泡烂了。”
监护仪的警报声响起时,李砚看见师傅的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雨点砸在医院的玻璃上,节奏跟当年锻工车间的小锤敲钢坯一模一样。
三天后,李砚在师傅的旧木箱里翻到半根磨秃的钢钎。钎头弯着,母亲说这是1990年修高炉时断在炉眼里的,师傅硬是用手抠了半小时,掌心磨得血肉模糊,却攥着断钎对父亲说:“老李,这玩意儿比奖状金贵。”
现在,李砚站在三号档案室的铁柜前。绿漆皮掉得露出褐色的铁,像师傅手上褪不去的老茧。钥匙插进锁孔时,他想起师傅总说的“开老铁柜得顺着力道,跟哄老机床似的”。果然,咔嗒一声后,柜门没动,得再轻轻晃一下,就像当年师傅教他开C620车床,总要先拍两下机身,让它醒透了再干活。
柜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混着酱油香的纸味飘出来,李砚的鼻子一下子酸了。父亲总爱在画图时叫米粉店的外卖,油星子常溅在图纸上,母亲骂他不爱干净,他却把溅了油的图纸叠得整整齐齐,这是烟火气,图纸有了这个,才知道是给谁造的。
松木盒就放在铁柜最里头,盒盖裂着道缝,是父亲用厂里的旧刨子亲手刨的,木纹里还卡着点红漆,是1989年刷技术革新小组牌子剩下的。打开盒子,最上面是本硬壳笔记,封面被手指磨得发毛,第一页的钢笔字却依然挺括:“1992年3月15日,跟老周在车间吃米粉,他嗦粉时说三峡要涡轮壳,外国专家说咱衡阳造不了,我跟他赌了碗米粉,说肯定能成。”
李砚的指尖蹭过纸页,摸到个硬疙瘩,翻过来一看,是半粒干硬的米粉,卡在涡轮壳三个字的缝隙里。再往下翻,蓝晒图纸的边角卷着,冷却水道那栏画了三道波浪线,旁边用铅笔写着:像湘江春汛的水纹,得顺着走,不能硬拦。右下角的签名日期是1993.6.8,离父亲心梗去世,只剩九天。
最后一张图纸的浇口处,画着个暖水瓶的简笔画,旁边还有道歪歪扭扭的小火车,是李砚五岁时画的。他记得那天趴在父亲腿上,拿铅笔在图纸边角乱涂,父亲没骂他,反而把小火车描得更清楚:“咱儿子这是给工业设计添了新花样。”
李工,这手绘图纸能当饭吃?张浩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手里的平板电脑亮着刺眼的光,屏幕上是智能铸造研究院的三维模型,昨天试铸又崩了,缩松孔比上次还大,德国专家说咱的参数全错了,院长都要发火了。
李砚默默卷起图纸,米粉渣掉在钢渣地上,他没捡,就像父亲当年说的好图纸得带着点生活印子,不然跟块冷钢似的。回到研究院,实验室的灯晃得人眼晕,新到的德国传感器闪着绿光,可桌上的涡轮壳铸件,还是带着个丑陋的缩松孔,像谁在上面狠狠按了个坑。
你们看这冒口设计。李砚把图纸铺在投影仪上,蓝晒纸特有的幽光映在墙上,我爸算过,金属液从冒口往下流,得跟湘江涨水一样,一层一层补。你们软件算的是直线,可铁水有脾气,它不喜欢走直路。
张浩皱着眉抚摸铸件:“可温度怎么定?传感器显示1500℃,浇铸出来还是有问题!”他的声音拔高了些,“李工,不是我不信老图纸,可现在是智能时代,总不能靠手摸眼看吧?”
话音未落,实验室的警报突然尖锐响起,智能机械臂的夹具卡壳了,铸件悬在半空,像个僵住的木偶。张浩急得满头汗,按了好几次紧急按钮都没用,德国专家远程指导也说“得拆了重装,至少两小时”。
让开。李砚突然掏出师傅那半根断钢钎,往夹具的缝隙里轻轻一塞。他记得父亲笔记里写着"老机床卡壳,得用软劲撬。果然,钢钎轻轻一别,夹具咔嗒响了声,立即恢复了正常。张浩愣在原地,看着李砚手里的断钢钎:这……这破钎子还能用?
不是破钎子,是老经验。王伯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人手里攥着个满是茶垢的搪瓷缸,“崽伢子,你们光看传感器,没摸铸件的温度吧?这铸件表面凉,里头还热,说明金属液没流匀,跟当年老李家说的冷芯热壳一个理。”
王伯是厂里的老炉工,今年八十二了,听说李砚在试父亲的图纸,特意拄着拐杖赶来。他伸手摸了摸有缺陷的铸件,指腹仔细蹭过缩松孔:“你爸当年遇到这情况,会在冒口旁边加个小浇道,跟给湘江支流开个小口似的,让铁水流得慢些。”
李砚突然想起父亲图纸里的暖水瓶简笔画,暖水瓶双层保温,浇口要是也做双层,不就能让铁水保持温度?他立刻着手修改图纸。张浩一开始强烈反对:“这老办法没数据支撑,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可连续两次试铸失败后,他也泄了气,只好跟着李砚一起改模型。
第三次试铸那天,湘江上飘着薄雾。机械臂握着双层浇口模具缓缓落下时,李砚紧攥着父亲的笔记,王伯在旁边紧盯火色:“亮白了,再等会儿……橘红了!就是现在!”当铸件终于取出时,张浩拿着卡尺量了又量,突然失声大喊:“误差0.02毫米!没缩松!没冷隔!”
消息很快传到经开区。管委会的人当天就来考察,他们仔细端详父亲的图纸,又听王伯讲述当年技术革新的故事,当即拍板:“老冶金厂的三号车间不拆了,改造成工业记忆馆,让游客亲眼看看衡阳是怎么从敲钢钎走到智能臂的。”
记忆馆开馆那天,李砚把师傅的断钢钎、父亲的暖水瓶壳,还有那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并排陈列在展柜中。展柜旁,王伯正带着一群孩子体验观火色,老人用迷你熔炉烧着铁块,耐心教孩子们分辨亮白是1600℃,橘红是1500℃。孩子们的小手在安全距离外比划着,就像当年的李砚趴在父亲身边看图样。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在图纸前驻足良久,突然拉住李砚:“我是张建军的儿子,当年你爸跟我爸一起画过涡轮壳图纸!我在深圳做工业设计,今天看到这些带着米粉渍的图纸,我想回衡阳开工作室了。”李砚指了指展柜里的钥匙:“这钥匙开的不是档案室,是咱衡阳人的工业根。”
傍晚时分,湘江上的雾气渐渐散去,记忆馆的灯光次第亮起,与对岸智能产业园的霓虹连成一片。楼下米粉店的香味袅袅飘来,老板是王伯的儿子,特意在记忆馆设了个车间米粉角,还原当年工人们在车间就着图纸吃米粉的场景。
李砚站在露台上,手中摩挲着那把锈钥。钥匙上的钢渣蹭在掌心,粗糙的触感让他想起父亲的手。他仿佛听见师傅在问:“小砚,图纸做完了?又听见父亲爽朗的笑声:”没做完呢,工业这事儿,得一代接一代添东西,哪有做完的时候?"
江面上,渔船的灯火渐次点亮,像是星星落入了水中。李砚轻轻抚摸口袋里的断钢钎,忽然明白了:衡阳的工业之光,从来不是冰冷的图纸或智能设备,而是师傅攥着断钢钎时手上的老茧,是父亲图纸上永远擦不掉的米粉渍,是王伯教孩子观火色时的耐心,是张浩从质疑到信服的转变——这些带着人间烟火气的东西,比钢水更炽热,比时间更持久,在湘江边,永远亮着,永远传承。
专业定制代写小品、相声、话剧、舞台剧、戏曲、音乐剧、情景剧、快板、三句半、哑剧、双簧、诗朗诵、演讲稿、微电影、动画等各类剧本。联系电话:13979226936 QQ:652117037 公众号:原创剧本网-剧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