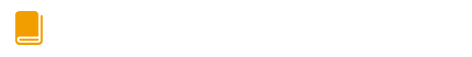
 剧本app下载
剧本app下载
 剧本公众号
剧本公众号

鲤城的天空,像是被岁月随手泼了层淡墨,晕染开一片沉静的灰青。鳞次栉比的瓦片层层叠叠,一直铺到天边,每一片都压着沉甸甸的年岁,砖缝里嵌着海风咸涩的吻痕。林羽拖着行李箱,轮子在西街坑洼的石板路上磕磕绊绊,发出沉闷的咕噜声,像在叩问这座沉睡古城的门扉。他停下脚,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搅和着海腥、老墙青苔的湿气、炸醋肉的焦香,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时光本身的沉静,丝丝缕缕,钻进肺腑。
街两边是连绵的“出砖入石”老墙,红砖与灰白的花岗岩犬牙交错,被风雨洗刷得色彩斑驳,却异常硬朗,像鲤城老人豁了牙却依旧硬气的笑容。骑楼下的店铺早早开了张,金纸铺里金箔晃眼,老药铺飘出草药的清苦,古厝茶馆溢出铁观音的暖香……店主们用抑扬顿挫的闽南话打着招呼,声音在狭长的巷子里撞来撞去,织成一张温热的网。一个阿婆坐在自家门廊的小竹椅上,眯着眼,慢条斯理地补一件靛蓝布衫,脚边蜷着一只打盹的狸花猫。这幅活生生的市井图,瞬间熨平了林羽心里从钢筋森林带来的最后一点焦躁和飘忽感。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鲤城啊,是活的。它的魂在这些巷子里,在这些厝边头尾的烟火气里,在每一块有故事的砖瓦木头缝里。” 他拖着箱子继续走,目的地是开元寺后巷的鲤城古建修缮所,脚步不觉轻快起来,不像远归的游子,倒像一只归巢的倦鸟,终于落回了自己的枝头。行李箱里那张“国际新锐修复师”的名片,在鲤城温吞的风里,显得那么轻飘,一吹,便彻底沉进了心底那个被乡愁填满的角落,没了声息。他丢下那个光鲜的职位,只为这座城,也为了父亲临终前那声悠长又带着不甘的叹息,还有那双再也握不住刻刀、却固执地指向故乡方向的手。父亲林振声,曾在这里,为开元寺的木梁耗尽半生,雕琢的不只是木头,更是对这座城的赤诚。现在,林羽回来了,带着在大洋彼岸淬炼的精湛手艺,和一颗比手艺更滚烫的心。
鲤城古建修缮所,门楣低矮,漆皮剥落,却像一座通往旧时光的微缩城门。林羽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迈了进去。一股独特的气息扑面而来,撞进鼻腔——陈年木屑的干燥味儿、桐油清冽的辛香、旧书纸淡淡的霉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来自开元寺的香火余烬。这味道熟悉又陌生,一下子把他拽回童年父亲那间永远飘着木头香的小屋。他的目光立刻被院中一位老者钉住了。老人身形精瘦如老松,白发如雪,精神头却极好,正弯腰凑近一段朽得厉害的木头构件,神情专注得像在端详稀世珍宝,外界的嘈杂都被他隔在了身外。那双粗糙的手,爬满岁月和木刺刻下的沟壑,极其轻柔地抚过木头的纹理,动作缓慢而郑重,仿佛指腹下流淌的不是木头,而是凝固的时光,他在与几百年前的匠人隔空低语。
“陈工!歇口气!看看谁来了!” 所长洪亮的声音打破了院里的沉静,他笑着迎上来,“新来的小林,林振声工长的儿子,林羽!国外学成回来的高材生!”
陈守拙的动作纹丝未动,像没听见。直到把那块朽木的每一条纹理都刻进眼里,他才缓缓地、极其缓慢地直起腰。他的目光,没有久别重逢的热乎,也没有对“高材生”的期许,反而像一把用旧了的、冰冷又精准的木工尺,在林羽年轻的脸上细细刮量。那眼神里全是审视,像在掂量一块待雕的硬木,不知里面藏着要命的蛀孔还是暗伤。过了半晌,才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干涩得像砂纸摩擦的“嗯”字。“林工的手艺,”他开口,声音低哑,目光扫过林羽干净却略显单薄、还没被工具磨出厚茧的手,“可不能糟践了。” 说着,他随手抄起工作台上他惯用的一把小巧平凿——木柄已被汗水和岁月浸得油亮发黑——又拣了块硬实的黄杨木边角料,丢到林羽面前的工作台上,“啪”一声,不容置疑。“试试手。雕个‘螭虎’。”
“螭虎?”林羽心头一紧。这可比寻常的缠枝莲、卷草纹难多了!螭虎是闽南古建木雕里的祥兽,讲究威猛灵动,鬃毛飞扬,爪牙带风,对线条力度、肌肉饱满和神韵要求极高,是检验匠人功底和悟性的硬杠杠。
“怎么?你爹没教过?还是洋墨水喝多了,把祖宗吃饭的家伙丢净了?”陈守拙眼皮都没撩,语气平淡,字字却像针,扎得人难受。他自己拿起一把半圆锉,对付起另一段木头里的蛀孔。
林羽胸口一堵,一股委屈掺着不服的热气往上涌,又被他生生压了下去。他没再吭声,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把院里沉淀的匠气都吸进去。他凝住神,拿起那把还带着陈守拙手心余温的平凿。刀锋切入硬实的黄杨木,手感生涩,远不如他惯用的高速电刻刀听话。他努力回想父亲笔记里关于螭虎形态的图样和运刀诀窍——“力贯指尖,意在刀先,顺木纹筋骨而行”。汗珠子慢慢沁出额头。时间在刻刀的游走和木屑的簌簌飘落中淌过。当他终于将一个略显生涩却筋骨初显、透出几分凶猛雏形的螭虎雕出来时,陈守拙停下了手里的锉刀,只撩起眼皮扫了一眼。
“嗯。”又是那声辨不出滋味的鼻音。他把一沓厚重如城砖的开元寺大殿残损测绘图纸推到林羽面前。图纸泛黄发脆,边角卷起,布满深褐色的霉斑,像岁月凝固的泪痕,虫蛀的小孔密如星点。他指了指角落那张堆满旧工具、蒙着薄尘的工作台——那是父亲曾经的位置。“先看,看透了再说。刀,”他用锉刀点了点林羽雕的螭虎,目光锐得像锥子,“不是那样飘的。要沉下去,吃进木头的筋里去,刻进它的魂里。” 语气依旧严厉,却似乎藏着一丝极淡的、几乎抓不住的指点味道。
图纸沉重得压手。林羽的指尖微微颤抖,抚过那些褪色的墨线和精准的标注。那熟悉的、略带飞扬的笔锋,分明是父亲林振声的字迹!图纸上仿佛还残留着父亲伏案时的气息。一瞬间,巨大的酸楚和思念直冲鼻尖,眼前一片模糊。他用力眨眨眼,把那股热流逼回去,深吸一口混着陈纸和木香的空气,强迫自己扎进这片由线条、数据和父亲心血汇成的、浩瀚复杂的图海。
几天后,林羽抱着一摞需要查对的图纸去资料室,路过修缮所临街的小院。院墙不高,墙外就是烟火缭绕的后街。他听见墙外几个阿公阿嫲带着浓浓闽南腔的闲聊声,清清楚楚飘进来。
“听说了没?开元寺大殿那根顶顶要紧的‘三步梁’,陈师傅他们愁得眉头能夹死苍蝇好些日子喽,虫蛀得厉害咧!像被‘粉虫’掏空了心!”一个沙哑的男声满是忧虑。
“作孽哦!那可是咱鲤城的命根子!六百多年的宝贝!比咱这些老骨头加起来都老!”一个阿嫲的声音又急又心疼,“陈师傅一把年纪了,可经不起再像当年林工那样,为了修梁把自己熬干喽…”
“呸呸呸!乌鸦嘴!莫乱讲!”另一个洪亮的声音立刻打断,带着不容置疑的维护,“政府不是拨了钱在修吗?咱厝边头尾也得把招子放亮点,自家门口、巷子头尾的古厝老墙,哪不对付,墙皮掉了、木头朽了,赶紧给修缮所递个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大家的事!”语气斩钉截铁。
林羽的脚步在青石板上顿了顿,心头涌起一股温热的暖流。原来,守护这座城的,不止是修缮所里这些拿着工具的人。这份朴素的关切、这份视为己任的自觉,本身就是一股无声却强大的力量,如同古厝的地基,深埋在鲤城的烟火里。这份“共建共管”的根,早就扎进了鲤城寻常巷陌的泥土里。
开元寺大殿内,光线幽暗静谧,时间在这里仿佛被香火熏得格外粘稠。高高的穹顶下,弥漫着古老木料深沉的松脂香、经年香火熏出的沉郁气息,还有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浮动的微光。林羽仰头,屏住呼吸,目光沿着那些层层叠叠、鬼斧神工般的叠斗拱,沿着那些粗壮如虬龙、扛着六百年重量的梁枋,缓缓向上爬,心中充满难以言喻的敬畏。个体的渺小与历史的宏大在此刻猛烈碰撞。
陈守拙的声音在空旷寂静的大殿里低沉响起,带着奇特的共鸣,仿佛从历史的夹缝里传来:“瞧见没?这‘偷心造’的斗拱,”他指向头顶精妙的木构,“看着精巧单薄,省料省工,却是老祖宗的大智慧!就靠着这‘偷’来的巧劲儿,稳稳撑起了鲤城六百多年的风霜雨雪,雷打不动!”他粗糙的手掌重重拍在身边一根需两人合抱的巨柱上,发出沉闷的回响,像叩响了历史之门,“这柱,叫‘梭柱’,中间鼓,两头收,线条顺溜,像不像咱鲤城老船公手里那支劈风斩浪的船桨?稳稳当当,任凭岁月冲刷,根基永固!”
他的脚步在一根巨大的梁枋下停住。光线在这里有些黯淡。陈守拙的目光变得异常柔和深邃,像在看一个故人。他指着梁枋与柱头交接处一块色泽明显较新的补木,声音陡然轻缓下来,带着一种近乎倾诉的低沉:“看看这‘鱼鳞榫’,小子。这可是你爹林振声的手艺,独一份。”他顿了顿,仿佛回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年夏天,也是这么一场没头没脑的泼天大雨,雷打得像天要裂开。这根梁,就在那个位置,‘咔嚓’一声,裂了道大口子,雨水像瀑布一样往里灌,下头的彩绘眼瞅着就要泡汤!你爹…他当时正烧得滚烫,可二话没说,抄起家伙就往上爬!梯子滑得像抹了油,雨大得睁不开眼。他在那梁上,在雨里泡了大半宿!就凭着一盏马灯那点豆大的光,硬是生生雕出这个‘鱼鳞榫’,严丝合缝地嵌进去,把裂口死死锁住!水,一滴也进不去了。”陈守拙浑浊的眼底,一丝难以捕捉的波动迅速掠过,像深潭投进一颗石子,涟漪很快又归于深沉的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汹涌的往事。“后来…他自己躺了三天三夜,烧得脱了形,人都走了样。”最后一句,轻得像一声叹息。
林羽浑身一震,猛地抬头,目光死死锁住那块嵌入深沉古木中的“鱼鳞榫”。在幽暗的光线下,那精巧绝伦的鳞片状榫舌紧密咬合着母卯,层层叠叠,环环相扣,仿佛它们生来一体。那不只是木头与木头的结合,更是父亲意志在岁月里的永生,是他对这座古城倾尽心血、舍命守护的见证!一股滚烫的热流夹杂着酸楚与难以言喻的骄傲冲上心头,他下意识地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
回到工坊,林羽小心翼翼地搬出父亲遗留下来的那个沉甸甸的樟木工具箱。箱子表面布满划痕和桐油渍,锁扣是古朴的黄铜。他屏住呼吸,轻轻打开。箱内,凿、铲、锉、锯、尺、规……各种工具摆放得整整齐齐,虽已多年未动,落了一层薄尘,但在林羽眼中,它们如同沉睡的兵器。他拿起一把柄身被父亲手掌磨砺得光滑圆润、仿佛有了包浆的弧形刻刀,刀柄上似乎还残留着父亲的温度与汗渍,那熟悉的触感带着血脉相连的力量,瞬间传递到指尖。
他铺开一张崭新的绘图纸,依据大殿内真实的残损测绘数据,结合父亲笔记里那些充满智慧与经验的批注和图解,开始潜心设计新的修复构件。核心,便是那结构精巧复杂、堪称古建木作巅峰的“鱼鳞榫”。铅笔在纸面沙沙作响,线条从最初的犹豫试探,逐渐变得流畅肯定,如同被注入了灵魂,在纸上勾勒、盘旋、交错。
无数个焚膏继晷的日夜过去,工坊的灯光常常是巷子里最后熄灭的一盏。林羽终于将精心绘制、反复修改的图纸和用上好楠木边角料试做的几个小型“鱼鳞榫”样品,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期待,轻轻放在陈守拙那张永远堆满旧图纸、木块和工具的工作台一角。陈守拙正全神贯注地对付一段内部被粉蠹虫蛀蚀得如同蜂窝的朽木,眉头紧锁,头也没抬,仿佛没看见林羽的到来和他放下的东西。空气里只有锉刀刮削朽木的刺耳声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陈守拙用镊子夹出最后一条顽固的蛀虫,才直起有些僵硬的腰,目光落在林羽的图纸和榫卯上。他拿起图纸,对着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天光,眯起那双锐利如鹰隼的老眼,仔细端详着每一个标注、每一根线条。接着,他又拿起一个榫卯样品,粗糙的手指反复摩挲着榫舌的每一个弧面、肩部的每一寸转角,感受着咬合面的平整度与角度。大殿内静得能听到灰尘落地的声音。半晌,他放下东西,拿起自己的卡尺,在林羽样品榫肩的某个位置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图纸标注,然后才淡淡地,近乎冷酷地丢下一句:“榫肩这里,厚了半粒米。吃不住长久的力。刀,”他抬眼,目光如炬地看向林羽,“还欠点火候。心,还不够静。”
半粒米!林羽愕然,如同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他拿起自己的卡尺,反复测量那个位置,又急切地对照图纸上的标注。那一刻,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修复古建不是艺术创作,容不得半分浪漫的误差。精确,是融入血液的本能,是对历史的绝对负责。这“半粒米”,是技艺的鸿沟,更是心境的差距。当晚,工坊的灯一直倔强地亮到深夜。窗外的鲤城早已沉入安详的梦乡,只有林羽的刻刀在坚韧的木料上低吟浅唱。父亲工具箱里的工具,在他手中一件件苏醒过来。一刀,复一刀,摒弃浮躁,心神合一。木料在沉稳的刀锋下逐渐驯服。当最后一个新做的样品,带着温润的光泽,严丝合缝地嵌入母卯,发出一声轻微而无比笃实的“咔哒”轻响时,汗水早已浸透了林羽的鬓角和后背,但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澄澈的喜悦和踏实感。
然而,鲤城古建的守护之路,从来不会只有平静的钻研。盛夏的暴雨,如同蓄谋已久的突袭,毫无预兆地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带着千钧之力,疯狂地砸在开元寺古老而巨大的筒瓦屋顶上,发出密集如战鼓擂动般的轰鸣,整个大殿似乎都在雨水的重压下微微震颤。就在这震耳欲聋的雨幕声中,一声沉闷、压抑、如同骨骼断裂般的不祥巨响,穿透重重雨帘,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殿内每一个人的心上!
“不好!”陈守拙脸色瞬间煞白,厉声嘶吼,声音在雷雨声中几乎被撕裂:“快!撑木!油布!护住彩绘!”
抢险的号角瞬间吹响!殿内人影晃动,气氛紧张得如同绷紧的弓弦。工人们吼叫着,扛起碗口粗的支撑木,毫不犹豫地冲进从瓦缝如注泻下的雨帘。巨大的油布被迅速抖开,在狂风中猎猎作响,数人合力才能勉强将其覆盖在可能出现险情的区域。然而,大殿深处,那根承受着巨大屋架压力的关键老梁——正是之前发现虫蛀隐患的位置——在湿气浸泡与内部结构被严重削弱的双重打击下,终于发出了绝望的呻吟!一道狰狞的、足有尺余长的裂口赫然出现!浑浊的雨水正顺着裂缝,如同贪婪的毒蛇,冰冷无情地涌向下方那些历经数百年沧桑、色彩依旧绚丽的珍贵天花彩绘和斗拱彩画!情势千钧一发!
“不行!光靠外面撑顶不住!裂口在里面!水在往里灌!”陈守拙目眦欲裂,吼声嘶哑如破锣,带着前所未有的焦灼和破釜沉舟的决绝,“必须立刻从内部加固!上穿枋!塞榫头!堵死裂口!把水给我截住!” 他的目光急速扫过身边几个年轻力壮的工人,然而这项任务需要的不仅是力气,更需要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精准操作的技艺、对古建结构的深刻理解,以及面对高空险境的巨大勇气!年轻工人们看着那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高梯和梁上狰狞的裂口,脸上都露出了本能的畏惧和迟疑。陈守拙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我去!” 林羽的声音并不高亢,却在嘈杂的雨声和呼喊声中异常清晰地穿透而出,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他猛地抹了一把脸上冰冷的雨水,目光灼灼,如同燃烧的炭火,直直迎向陈守拙惊愕、审视、继而变得无比锐利的眼神,“那‘鱼鳞榫’的结构,我最熟!裂口的位置和角度,只有我能处理!让我上!”
时间仿佛被这暴雨冻结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羽身上。陈守拙死死地盯着他,眼神复杂如漩涡,锐利如刀,又似在燃烧。他看到了林羽眼中那份与他父亲当年如出一辙的、近乎偏执的担当!终于,在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声中,陈守拙猛地一跺脚,浑浊的泥水四溅,他用尽全身力气,几乎是咆哮着,吼声压过了雷声:“好!梯子!快!给他扶稳了!用命扶!” 那吼声里,带着孤注一掷的信任,带着托付一切的沉重,也带着一丝深藏的恐惧。
冰冷的、被雨水浸透的木梯,踩上去滑腻异常,在狂风暴雨中不住地剧烈摇晃。林羽背着沉重的工具袋(里面是硬木料、刻刀和小锤),手脚并用,牙齿紧咬,向上攀爬。狂风卷着冰冷的雨水,像无数鞭子劈头盖脸地抽打下来,眼睛根本无法睁开。他只能完全依靠指尖的触感,在湿滑冰冷、布满历史沟壑的梁木上摸索。高处,那根开裂老梁在巨大应力下发出的“嘎吱…嘎吱…”呻吟声近在咫尺,每一次异响都让脚下的木梯剧烈震颤。下方,陈守拙那双布满青筋的手,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如同焊铁般死死地、用整个身体的重量把住湿滑的梯脚。那股从梯身传递上来的支撑力和微微颤抖的力道,是林羽此刻唯一的支点。
他终于够到了那狰狞的裂口!浑浊的雨水正从裂开的木头深处不断涌出。林羽迅速抽出硬木料和那把父亲传下的弧形刻刀。他深吸一口气。当刀锋触及湿滑木头的刹那,世界的声音仿佛消失了。他的眼中只剩下这道历史的伤口。刀锋在湿滑的木头上精准游走,木屑混合着冰冷的雨水簌簌落下。他闭上一只眼,仅凭指尖的感觉和记忆中的图纸,在极狭小、湿滑、充满危险的空间里,将新雕出的“鱼鳞榫”雏形奋力嵌入那不断呻吟的伤口深处!
“锤子!” 林羽头也不回,声音嘶哑地向下喊道。
一只沾满冰冷雨水和污泥、微微颤抖却异常有力的手(是陈守拙!)立刻将沉重的木槌递了上来。林羽紧紧握住那湿漉漉的木柄。他调整呼吸,用尽全身力气和技艺赋予的巧劲,对准榫头暴露在外的部分,狠狠一锤!再一锤!沉闷而坚定的敲击声在雷雨轰鸣的短暂间隙中顽强地震荡开来!每一次重击,都伴随着脚下木梯令人心胆俱裂的剧烈震颤,以及下方陈守拙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的、压抑而痛苦的闷哼!
汗水、雨水模糊了林羽的双眼。手臂早已酸痛麻木。肺叶如同破旧的风箱。就在他感觉最后一丝力气即将耗尽,意识开始模糊的边缘,他凝聚起残存的全部意志,发出一声压抑的嘶吼,手中的木槌带着千钧之力落下!
“咚——!”
最后一声敲击,仿佛带着悠长的回音。奇迹发生了!那嵌入裂口深处、层层咬合的“鱼鳞榫”,终于严丝合缝地锁紧!裂缝扩张的恐怖“嘎吱”声戛然而止!汹涌的雨水,再也无法从这道被强行弥合的伤口肆意侵入!
成功了!
林羽整个人如同被抽掉了骨头,虚脱般地瘫软在冰冷湿透的梁木上,胸膛剧烈起伏。他艰难地侧过头,低头望去。梯子下,陈守拙依旧死死地仰着脸,密集的雨线冲刷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庞。他紧抿着毫无血色的嘴唇,没有欢呼,没有说话。只是那死死把住梯脚、关节处因过度用力而一片惨白、仍在微微颤抖的双手,暴露了一切。在那双被雨水和疲惫模糊的苍老眼睛里,林羽分明看到了一种近乎碎裂的紧张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东西——一种沉重的、超越言语的认可与托付,比任何勋章都更重,更深地烙进了他的灵魂。那眼神仿佛在说:这担子,你接住了。
雨势终于渐歇,只剩下屋檐滴水的嗒嗒声。大殿内弥漫着浓重的湿木气息、新鲜的桐油灰味道,还有一种汗水和紧张褪去后的宁静。极度的疲惫瞬间将林羽淹没。他蜷缩在角落一捆相对干燥的防雨油布上,意识沉入黑暗。朦胧间,他感觉一件带着体温、厚重而粗糙的外套,带着熟悉的陈年木屑和淡淡汗味,轻轻地覆盖在他冰冷湿透的身上。他费力地掀开沉重的眼皮缝隙——逆着窗外透进的微薄晨曦,一个清瘦而略显佝偻的熟悉剪影,正慢慢地转过身,走向大殿**那根刚刚获救的老梁。正是陈守拙。
陈守拙长久地、近乎贪婪地仰头凝视着梁上那块新嵌入的、色泽尚浅的补木区域。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没有抚摸,而是极其轻柔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指腹感受着新老木料在“鱼鳞榫”处完美咬合的细微起伏。那动作里蕴含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和失而复得的珍视。大殿里静极了,只有他指尖摩挲木头发出的细微沙沙声。
“你爹当年,”他沙哑疲惫的声音忽然响起,在空旷寂静的大殿里带着回响。他并未回头看林羽,更像是说给那根沉默的梁、说给这殿里的木头听,“爬的是东边那根更陡、更滑的梁……雨,比今晚还大,雷就在头顶炸……你这小子,”他顿了顿,手指停留在新木浅黄与老木深褐完美交融的咬合线上,“比你爹……胆大。” 短暂的沉默后,那个字,轻微得如同一声悠长的叹息,却又带着千钧之力,瞬间烫进林羽心底:“这‘鱼鳞榫’……做得……好。”
那一个“好”字,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酸楚与滚烫交织的热浪猛地冲上林羽的眼眶。他慌忙闭上眼,将脸更深地埋进那件犹带着老人体温、散发着陈年木屑和汗味的粗糙外套里。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彻底放松。
雨彻底停了。一缕清澈纯净的金色晨曦,穿透古老的木格窗棂,斜斜地照射在大殿**那根劫后余生的老梁上。光柱中,尘埃如同金色的精灵在舞动。那根承载着六百年风雨的老梁,新补的“鱼鳞榫”处,在初升朝阳的抚触下,泛着温润而坚定的微光。新木的浅金与老木的深褐紧密交融,宛如一道嵌入古城肌理的崭新年轮。
殿外,传来孩子们清脆的笑闹声。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老师和几位鬓发斑白的老匠人(其中一位正是之前墙外闲聊的老张)带领下,正围在一块刚从残损木构件上拓印下来的古老雕花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浸湿的宣纸覆盖在涂满墨汁的雕花上,用特制的拓包轻轻拍打。墨色在宣纸上氤氲开来,那流畅优美的缠枝莲纹样渐渐浮现。孩子们屏住呼吸,小脸涨得通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高高举起自己拓印的纹样,兴奋地喊道:“老师!看!我抓到啦!一条从木头里游出来的小鱼!”
她童稚无邪的欢呼,像纯净的泉水,穿透古老沉静的大殿,漾开一圈圈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涟漪。那一刻,倚在油布堆旁的林羽,和站在老梁下的陈守拙,仿佛都清晰地看见:鲤城——这座始终在呼吸着的古城,那些沉默的砖、古老的木、斑驳的痕,连同他们每一次屏息的雕琢、每一次奋不顾身的托举、每一次小心翼翼的拓印,都深深融入了这座古城悠长而坚韧的生命之中。那宣纸上拓印出的、源自“鱼鳞榫”边缘的抽象水波纹样,在女孩纯真的眼中化作了游动的小鱼,正是古老技艺在新一代心中种下的种子。
陈守拙缓缓转过身,初升的太阳洒满他苍老却刚毅的脸庞。那些刀刻斧凿般的皱纹在明亮的光线下显得深邃,却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柔和光芒笼罩。他看着那个高举拓片、笑容灿烂的小女孩,又看了看倚在角落、眼神明亮坚定的林羽。这个在木屑和桐油气息里浸泡了一辈子、习惯了以沉默和严厉包裹自己的老人,嘴角那个常年紧抿的线条,终于微微牵动了一下,向上扬起一个极其浅淡、却无比清晰的弧度。他抬起手,罕见地、带着一种郑重托付的意味,轻轻地、却无比坚定地拍了拍林羽沾着泥水、略显单薄却在此刻显得无比可靠的肩膀。
肩上传来的那沉甸甸的、带着老人体温和力量的一拍,让林羽心头剧震。他顺着陈师傅的目光,再次望向大殿深处那根沐浴在金色晨光中的老梁。那道嵌入其中的崭新“鱼鳞榫”,在朝阳下闪烁着温润而坚定的光芒,宛如一条金色的鲤鱼,逆着岁月的洪流,奋力跃过了时光的断崖。
林羽知道,鲤城的故事,远未结束;属于他们这一代人,以及未来无数代人的守护与续写,伴随着这晨光与孩童的笑语,才刚刚郑重启程。殿外,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着从老街巷深处隐约飘来的、悠扬婉转的南音古乐,交织融合,在雨后清新的空气中,回荡成鲤城新的一天最动人的序曲。这座城,将在无数双手的守护下,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书写它永恒而崭新的篇章。
专业定制代写小品、相声、话剧、舞台剧、戏曲、音乐剧、情景剧、快板、三句半、哑剧、双簧、诗朗诵、演讲稿、微电影、动画等各类剧本。联系电话:13979226936 QQ:652117037 公众号:原创剧本网-剧星
